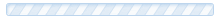
为何针对飞盘的“污名化”会与其“流行化”接踵而至,而对于一项体育运动而言,“流行”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谢廷玉 编辑 走走 校对 刘军
体育运动的“大众化”从来都有多条路径。在过去,乒乓球、广播体操、足球、骑行、跑步等都曾成为全民流行的运动。当然,每种运动流行的原因与背景各不相同。而当前,飞盘运动正凭借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迅速出圈流行。
在飞盘之前,从“郑多燕减肥操”到“刘畊宏女孩”,体育内容向流行文化的转变早已不再新鲜。然而,前者更多以个别“体育网红”为中心,其受众也主要以“玩梗”而非真正参与运动的形式介入其中。同时,其流行大多是一时火爆,较少产生深远影响。
相较之下,飞盘则是一项有组织、有规则的“运动”,许多宅家久坐的“办公一族”也真正被它吸引到了体育场上。更重要的是,飞盘的流行带来了长远成效——体育总局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展国内首届飞盘联赛。那么,一项体育运动的风靡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其流行之始,飞盘就面临着“文化变味”乃至被“污名化”的风险。“飞盘局”演变为“相亲局”和“拍照局”的事例屡见不鲜,更有飞盘玩家被贴上“飞盘媛”的标签。在相当程度上,飞盘以“景观”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并接受着凝视和评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为何针对飞盘的“污名化”会与其“流行化”接踵而至,而对于一项体育运动而言,“流行”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
运动的流行:
体育作为“共同文化”的表达
当人们在解释飞盘“走红”的成因时,大多将其归结为飞盘运动本身的属性。当然,这也的确是某一部分原因。正如《新京报》公众号文章《飞盘是啥?为啥突然这么火?》所提到的:“飞盘这项运动门槛不高,从两个人到20个人都可以玩,对场地和器材的需求也没那么苛刻,在社区的小广场、花丛边,甚至小路上都能玩起来,同时,它还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和社交性。”
然而,这样的理由仍不充分。一方面,许多比飞盘要求更低,且同样简单有趣的运动(例如许多人年幼时曾玩过的“丢沙包”)却并未如飞盘一般流行;另一方面,尽管入门容易,但这项运动的拥趸往往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并购买训练课程与优质器材。更有趣的“玩法”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文章《玩飞盘,只是拍拍照这么简单吗?》中所报道的:“他们会带着飞盘环球旅行,在贝加尔湖的冰上玩飞盘,裹着羽绒服在雪地里捡飞盘;他们会带着飞盘露营,一边乘着皮划艇和桨板水上漂,一边带着飞盘互相传递。”
无论飞盘本身具有怎样的属性,作为“流行文化”的飞盘已经与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绑定在了一起。相当多的飞盘玩家已经部分实现了“新中产阶级”——“财富自由”的企业员工或自由职业者,他们拥有闲暇的精力和多余的财力,追求富于创造力的生活方式和高质量的人际社交。正因如此,飞盘的流行首先是一种在特定人群之中的流行,正是借助这一群体的影响力,飞盘才得以进一步出圈并博得更多关注。
一种体育运动能在特定群体中流行,其原因不仅关乎它本身的属性,更在于它成功表达了这一群体的“共同文化”。飞盘的组织方式和游戏规则需要与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方式相契合;同时,该群体的成员能通过参与此项运动将自身塑造为其所认同的理想形象。在这种意义上,飞盘的流行与足球颇为相似——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足球也被广泛视为一项流行于无产阶级之中的运动。正是对足球与无产阶级之关系的考察,能为我们理解飞盘的流行提供线索。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870-1914》一文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到:“足球运动在当时崛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而且是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吸引众多观众的体育比赛,还出现了一种男性的足球文化,这一文化由于国王自1913年起出席足总杯决赛而得到了巩固。”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被足球吸引,正是因为其“共同文化”在足球中得到了表达。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可被概括为“身体荣誉观”和“地方性忠诚”的结合。正如布尔迪厄所评论的,无产阶级的“身体”是其最重要的资本,代表了“力量、速度和敏捷”;而资产阶级和中产者的身体则具有更强的“文明化特征”,力图展现出“社交自信和个体化的掌控能力”。正因如此,无产阶级通过凸显其“男性气概”来拉开与所谓“中产阶级傻帽”的距离——后者因“女性化”的教养和虚弱的身体而被认为缺乏“男性的骄傲”。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生活长期围绕着特定的工业城市和地区展开,因而他们更易产生对地方性共同体的归属感,并追求属于“本地”的荣誉。
不难看出,此种自我认同既能够在足球中获得表达,又塑造了一种具有无产阶级特色的足球文化:足球显然是一种适合于展现“男性气质”,并凸显“力量、速度和敏捷”的运动;足球比赛往往以地方为单位组建队伍,因而易被视为地方性荣耀的载体。同时,随着排他性的地方认同和“男性气质”中的暴力因素被引入足球运动,“足球流氓”的气质也构成了英国足球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一支足球队有着固定的位置分工和战术配合,其比赛也依靠专业的裁判和复杂细致的判罚规则而进行。在某种程度上,此种组织架构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模式也具有相当的同构性:严密高效的分工协作与高度“合理化”的规则体系构成了大工厂生产的突出特点。足球既与无产阶级的日常工作模式形成了呼应与契合,又能表达工人群体的“理想自我”,而足球也正是因为适于表达无产阶级的“共同文化”方得以风靡。
━━━━━
飞盘的“走红”:
“玩飞盘”与“新中产阶级精神”
对足球与无产阶级之关联的分析让我们获得了一种解释“流行运动”的普遍性视角:一种运动在特定群体中的流行缘于其对该群体“共同文化”的表达。如要采取这一视角对飞盘的流行做出更加具体的解释,就有必要阐明飞盘的玩家具有何种“共同文化”,而此种“共同文化”又如何在飞盘运动中获得了表达。
如前所述,大多数飞盘玩家来自于已部分实现了财富自由的公司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如若对他们的“共同文化”加以剖析,我们便将看到一种属于“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想象。
他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和19-20世纪的大工厂劳动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作者吕克·博尔坦斯基指出,相较于过往,当下的工作模式允许劳动者保有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他们在劳动时已经不再是按照流水线的要求进行片段化的重复作业,而是可以自主开展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他们也没有被限定在某个机械的分工环节之中,而是可以随时与自己的同事展开商讨和协作。这种劳动模式强调自发的创造力,鼓励工作者将自己的想法“注入”工作流程,而非一味遵循既定准则。因此,它进一步弱化了外部的监管和规制,而强调内生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不难发现,这样的工作模式恰恰和飞盘的规则有着契合之处。不同于足球比赛中每支队伍必须满足一定的人数要求,飞盘是一种“从两个人到20个人”都能灵活玩转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正可以与工厂“流水线”与当代公司中“项目组”的差异相类比,后者可以项目为导向,灵活配置人手。飞盘比赛虽有规则,但可以不设裁判,让场上选手自行裁决。此种“自判”规则恰与当代企业弱化外部监管规制,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机制相映成趣。
除此之外,飞盘比赛中虽然也有“控盘”和“接盘”的分工,但相较于足球等运动,此种划分相对模糊了许多,让玩家有很大的空间自主拟定策略。如此便可以解释,为何许多办公室白领甫一接触飞盘便觉得与它“一见如故”——这不仅是因为飞盘本身容易上手,更是因为其规则的底层逻辑与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样态颇有类似。
当代新中产阶级的“理想自我”也能在飞盘运动中找到表达的出口。对这一群体而言,其“理想自我”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强调“自我实现”的可能——这意味着以文明、自律且富有审美意味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其二则是注重“主体间性”的确立——这意味着在“工作之交”以外,他们还试图和他人建立起健康稳定,具有个人性的人际交往关系。
而上述的“理想”都能被飞盘运动捕捉。已经有许多玩家意识到了飞盘的“文明化”和“审美化”特征。相较于足球和篮球等身体对抗激烈的运动,飞盘恰恰以“避免身体接触”为基本规则。在飞盘比赛中,选手被禁止阻挡对手的跑动,也不应遮挡对方的视野。不难发现,飞盘玩家想要在运动中展现的不仅是“力量、速度和敏捷”,更是一种时刻保持“自律”和“文明”的精神状态,也正因如此,飞盘弱化了在许多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男性气概”,而被视为一种男女可以同台竞技的游戏。同时,正如《三联生活周刊》所报道的,部分玩家格外看重“飞盘美学”——玩飞盘的姿势轻盈舒展,兼具力量美和线条美。
飞盘也开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社交空间。在足球、篮球比赛中,参赛者主要以相对固定的“队伍”为单位进行训练和比赛,从而和队内其他选手结成密切的“队友”关系。但在论及飞盘时,人们更多谈到的是“飞盘局”——这是一种类似于剧本杀“组局”的构成方式,其中可能会有几组互不相识的选手一同成队参赛,并在比赛的过程中逐渐熟识。
概言之,正因“飞盘”适合于充当新中产阶级“共同文化”的表达,它才在这一群体中流行开来。也正因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表现强势且广受追捧,飞盘运动的影响力也便由此扩散开来,逐渐形成我们当下所见的盛况。
━━━━━
飞盘的污名化:
不堪重负的“文化符号”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飞盘运动充当了“新中产阶级精神”的表达,进而成为了一种标定社会身份的“文化符号”,它才会不断遭受包括“污名化”在内的风险。在当前,飞盘运动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被归结为二:首先,它有可能蜕化为一种纯粹的“景观”;其次,它可能被其他功利性目的“殖民”。
飞盘局向“拍照局”的转变最好地说明了前一种风险。
作为文化符号的飞盘代表着广受追捧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在当下的“景观社会”中,一个人是否能真正玩转飞盘很少受到关注,重要的是他/她能否呈现出“参与飞盘运动”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又标定了一种备受欣羨的生活样态。因此,正如媒体公号《外滩TheBund》的文章《飞盘走红、污名化,我不敢说自己爱玩了》所报道的:“在任意社交网络搜索‘飞盘局’,大多数俱乐部都会表示价格包括请摄影师的费用。还有的专门以拍出美照为卖点,并会进行动作指导——这个指导不是为了把飞盘玩得更好,而是拍照的姿势更好看。”这样的“网红摆拍”既是一种对文化符号的“挪用”,也是一种对身份界限的“僭越”和“解构”,也正是在这样的解构之中,飞盘运动原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变得越发单薄。
飞盘局向“相亲局”和“社交局”的转变则有助于说明第二种风险。
这项运动所标定的身份意味着一系列适于在“婚恋市场”和“社交市场”待价而沽的“抢手商品”:飞盘所吸引的“新中产阶级”往往既有财富,又有闲暇,更拥有自律的品质和丰富的生活情趣。换言之,飞盘不仅是一项运动,更在特定的情境下充当着象征性资本,“飞盘玩家”往往被视为合适的婚恋对象与社交伙伴。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飞盘作为组建相亲局、联谊会的纽带也便不难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功利性的目的“殖民”并“挤占”了飞盘运动原有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服务于其他意图的手段。
同时,恰恰是两种风险之间的密切勾连使得飞盘运动易于蒙受“污名化”的困扰。正因“飞盘局”有助于实现其他功利性目的,因而才会有如此多的人尝试打造与飞盘有关的“表象”和“景观”,借以让自己融入到以“飞盘”为名的“相亲”或“联谊”活动,并在其中有所斩获。如此一来,所谓“飞盘媛”的出现和飞盘运动的“污名化”也便接踵而至。经由对文化符号的挪用和塑造,他们得以逾越既有的身份界限,并以此实现象征性资本的“原始积累”,攫取更多的文化和社会资源。
事实上,让飞盘运动维持其“本真性意涵”,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进一步的推广和“大众化”。
飞盘之所以易于遭受“污名”,正是因为其所标定的仍是一种带有精英色彩的,只有“小众群体”才能享受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获得了“象征性资本”的地位——对于飞盘运动而言,此种地位既是使之流行的关键,又是它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下,飞盘的流行仍以“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上的“强势”为前提,但如要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和“国民化”,则需要让那些无法在社交媒体上备受欣羨甚至发声的群体也能享受到这门运动的快乐和真意。而一旦达成了这样的“大众化”和“国民化”,围绕飞盘的“污名”也就将迎刃而解。